導(dǎo)語:險資的風險認知變革與治理體系修復(fù),往往并不發(fā)生在繁榮期,而是在失敗投資已經(jīng)造成實質(zhì)性巨額損失之后,才在陣痛中被迫展開。
作為華夏幸福經(jīng)營風險最大的承擔者之一,平安人壽在公司最高決策層的處境,依然十分被動。
12月22日,華夏幸福(600340.SH)公告稱,公司董事會以1票同意、7票反對、0票棄權(quán)的表決結(jié)果,決定不將股東平安人壽提出的五項臨時提案提交至202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;董事長王文學(xué)對上述提案均投出反對票。

圖源:華夏幸福公告
在華夏幸福重整進入深水區(qū)三年多后,作為持股比例最高、亦是風險敞口最大的單一機構(gòu)投資者,平安人壽仍未能在決定公司命運的核心治理問題上取得實質(zhì)性話語權(quán)。
2018年至2020年間,平安系(平安人壽及一致行動人)合計斥資約 180 億元入股華夏幸福,持股超 25%。

彼時的華夏幸福,仍被資本市場視為“產(chǎn)業(yè)新城”模式的標桿企業(yè),其商業(yè)模式深度綁定地方政府,以住宅地產(chǎn)開發(fā)的短期現(xiàn)金流反哺產(chǎn)業(yè)園區(qū)建設(shè)的長期投入。
在表面上,該模式與保險資金追求長期、穩(wěn)定資產(chǎn)配置回報的內(nèi)在邏輯,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契合。
險資擁有長久期的負債,需要尋找能夠穿越經(jīng)濟周期的長期資產(chǎn);而華夏幸福的產(chǎn)業(yè)園,一旦成熟運營,便能提供穩(wěn)定的租金與產(chǎn)業(yè)服務(wù)收入。
更重要的是,當時的宏觀與行業(yè)環(huán)境,為這一判斷提供了現(xiàn)實支撐。房地產(chǎn)尚未進入全面去杠桿階段,地方政府融資渠道仍相對通暢,信用環(huán)境并未出現(xiàn)系統(tǒng)性收縮。
在這一背景下,平安系的進入,更多被市場理解為“戰(zhàn)略型財務(wù)投資”——不追求控股,但通過資本加持獲得長期回報,同時為企業(yè)治理提供一定程度的“外部約束”。在那個階段,關(guān)于控制權(quán)、否決權(quán)和危機處置機制的討論,更多停留在合同條款層面,而非現(xiàn)實博弈。
于是,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被忽略了:在這樣一個創(chuàng)始人色彩濃厚、股權(quán)高度集中的公司里,治理結(jié)構(gòu)安排是否足以支撐平安系承擔的巨大風險?

圖源:同花順ifind
遺憾的是,這個問題,在行業(yè)的順周期中被增長的潮水所掩蓋。恪守“財務(wù)投資、不干預(yù)經(jīng)營”乃至只保留一個董事會席位的邊界感,卻在日后被證明是一種致命的疏忽。
轉(zhuǎn)折發(fā)生在2020年之后。隨著融資環(huán)境急劇收緊,華夏幸福的現(xiàn)金流結(jié)構(gòu)迅速惡化,大量債務(wù)集中到期,風險開始顯性化。2021年初,華夏幸福債務(wù)危機全面暴露,隨后進入重整程序。
當年 9 月,華夏控股持股因強制處置被動下降,平安系成為第一大股東,但華夏控股仍為控股股東,創(chuàng)始人、董事長王文學(xué)為實際控制人,平安在董事會僅有 1 個席位。

圖源:同花順ifind
此時,平安人壽的角色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:從順周期中的財務(wù)投資人,變成逆周期中最重要、也最被動的風險承擔方之一。
根據(jù)業(yè)績發(fā)布會與年報披露,截至 2021 年末,平安對華夏幸福總體風險敞口達 540 億元,當年計提信用減值損失 432 億元。

圖源:中國平安2021年報
高達數(shù)百億元的累計減值金額,是對資本實力、風險承受能力以及內(nèi)部風控體系的實質(zhì)性考驗。更為復(fù)雜的是,隨著重整推進,治理層面的矛盾開始集中爆發(fā)。
一個極為尷尬的結(jié)構(gòu)性錯配出現(xiàn)了—— “風險在我,控制不在我”。
作為第一大股東,平安人壽是華夏幸福風險敞口最大的機構(gòu),其投資的榮損與公司的存亡休戚與共。然而,在決定公司如何“療傷”、如何“求生”的關(guān)鍵決策上,它卻幾乎毫無影響力。這種權(quán)責之間的巨大不匹配,在華夏幸福進入債務(wù)重組階段后,被一系列事件急劇放大。
其一,是“置換帶”方案的爭議。2024年,華夏幸福提出一項復(fù)雜的資產(chǎn)騰挪方案,以 2 元對價向廊坊市資產(chǎn)運營管理有限公司轉(zhuǎn)讓兩家下屬公司,涉及225.75 億元對廊坊銀行債務(wù);資產(chǎn)置換后資產(chǎn)仍委托華夏幸福及其子公司運營,運營處置收益歸廊坊銀行,不達考核目標需現(xiàn)金補足。這相當于廊坊銀行的債權(quán)從原本的普通債權(quán)變成優(yōu)先債權(quán)。

圖源:華夏幸福公告
平安人壽派駐董事王葳在董事會與股東大會均投反對票,其后稱方案 “置換帶處理不審慎”,但該方案仍在董事會以微弱優(yōu)勢通過。這第一次清晰地暴露了平安在董事會層面的孤立與無力。

圖源:華夏幸福公告
其二,是預(yù)重整程序之爭。2025年11月,華夏幸福公告法院已受理其債權(quán)人龍成建設(shè)工程有限公司提出的預(yù)重整申請,平安系董事王葳公開聲明對此“完全不知情”,并稱,該公告的發(fā)布完全繞過其本人,嚴重違反了公司章程規(guī)定的董事會議事規(guī)則和公司治理的基本程序。這標志著雙方的矛盾已經(jīng)從具體方案的分歧,升級為對程序正義與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根本性質(zhì)疑。
其三,便是此次臨時提案的全盤被否。平安人壽提議新增五項臨時提案至 2025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,涵蓋重整事項決議級別、董事罷免與選舉、財務(wù)盡調(diào)配合、債務(wù)重組執(zhí)行說明等核心訴求,均被董事會被以1:7的懸殊票數(shù)否決。這徹底關(guān)閉了平安在董事會內(nèi)部解決問題的通道,也宣告了其作為財務(wù)投資人與創(chuàng)始人控制型企業(yè)之間,在危機情境下不可調(diào)和的權(quán)責張力已達頂點。
當年平安的入局并非草率。彼時宏觀經(jīng)濟穩(wěn)中向好,地方政府有強烈的招商引資與基建擴張沖動,房地產(chǎn)融資環(huán)境相對寬松,而險資監(jiān)管框架亦鼓勵其進行長期股權(quán)投資以優(yōu)化資產(chǎn)配置。
然而,當這些外部環(huán)境發(fā)生逆轉(zhuǎn),當“產(chǎn)業(yè)新城”模式中的地方財政與房地產(chǎn)銷售雙雙承壓時,被忽視的內(nèi)部治理結(jié)構(gòu)缺陷,便如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,引發(fā)了連鎖反應(yīng)。
這種在順周期中被掩蓋、在逆周期中被急劇放大的治理困境,并非孤例。2008年金融風暴中,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(AIG)的傾覆,提供了一個更為慘痛的參照系。
與平安人壽無法有效控制被投公司的“外部治理困境”不同,AIG的問題爆發(fā)于集團內(nèi)部。
其倫敦的一個小型部門AIG金融產(chǎn)品部,在總部視野之外,通過出售信用違約互換(CDS)這一復(fù)雜的金融衍生品,積累了天文數(shù)字的風險敞口。在次貸泡沫時期,這些業(yè)務(wù)被視為源源不斷的利潤奶牛,其風險模型被奉為圭臬,無人敢于挑戰(zhàn)。AIG總部對這個“治理黑箱”的實際風險,缺乏有效的認知與制衡。
在順周期中,風險被模型的樂觀假設(shè)與持續(xù)的盈利所長期低估,而治理機制,無論是外部的董事會監(jiān)督,還是內(nèi)部的垂直風控,均未能對已經(jīng)失控的高風險敞口形成有效制衡。
當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(fā),底層資產(chǎn)大規(guī)模違約,AIG瞬間被推向破產(chǎn)邊緣。最終,美國政府以超過1820億美元的代價出手救助。但救助并非沒有代價。
在政府的嚴苛要求下,AIG被迫進行了一場“斷臂求生”式的極端重組。AIG隨之全面收縮高風險的金融產(chǎn)品業(yè)務(wù)、重構(gòu)了從董事會到業(yè)務(wù)一線的風險管理與資本約束體系,更令人扼腕的是,它被迫出售了旗下最優(yōu)質(zhì)、盈利能力最強的“皇冠上的明珠”——亞洲業(yè)務(wù)友邦保險(AIA),以償還政府貸款。
2010 年,AIA 在香港聯(lián)交所上市,募資超 200 億美元,成為當時全球保險業(yè)有史以來規(guī)模最大的 IPO ,全球有史以來第三大規(guī)模的IPO、香港歷史上最大規(guī)模的IPO。所籌資金主要用于償還政府救助款。
回看平安人壽,可以看到某種相似的邏輯。
不同的是,平安人壽面對的不是復(fù)雜衍生品,而是實體企業(yè)治理結(jié)構(gòu)與債務(wù)體系交織形成的長期風險網(wǎng)絡(luò);其應(yīng)對路徑,也并未走向外部接管或激烈拆解,而是在市場化和法治框架內(nèi),通過提案、表決、博弈乃至訴訟,試圖為自身爭取更合理的風險處置結(jié)果。這一過程緩慢、成本高昂,卻更符合中國制度環(huán)境下的現(xiàn)實路徑。
無論中外,保險資金真正的風險認知變革與治理體系修復(fù),往往并不是發(fā)生在鮮花著錦、烈火烹油的繁榮期,而是在一筆具體的、失敗的投資已經(jīng)造成實質(zhì)性、巨額性損失之后,才在陣痛中被迫展開。
這場代價高昂的實踐課,正在迫使所有手持巨資的保險機構(gòu)重新思考三個根本性問題:
1.財務(wù)投資的邊界何在?
當投資額度巨大、風險高度集中時,純粹的“不干預(yù)”是否還是一種負責任的態(tài)度?
2.治理參與的深度應(yīng)達幾何?
在不能控股的前提下,如何通過投資協(xié)議、董事會席位安排和關(guān)鍵事項的否決權(quán),建立起有效的“風險防火墻”?
3.風險承擔的邏輯是否需要重構(gòu)?
除了財務(wù)模型,如何將“治理風險”、“創(chuàng)始人風險”和極端的“政策風險”納入核心考量?
平安人壽與華夏幸福的“權(quán)力游戲”尚未落幕,但它無疑已經(jīng)為下一階段中國險資的投資行為、風控邏輯乃至監(jiān)管政策的制度性調(diào)整,提供了深刻而有實質(zhì)意義的現(xiàn)實案例。
對于整個險資行業(yè)來說,在長期資金深度參與實體經(jīng)濟的過程中,真正需要被反復(fù)校驗的,并不僅是資產(chǎn)回報假設(shè),而是當周期逆轉(zhuǎn)時,資本是否擁有與風險相匹配的治理工具。(阿爾法工場金融家)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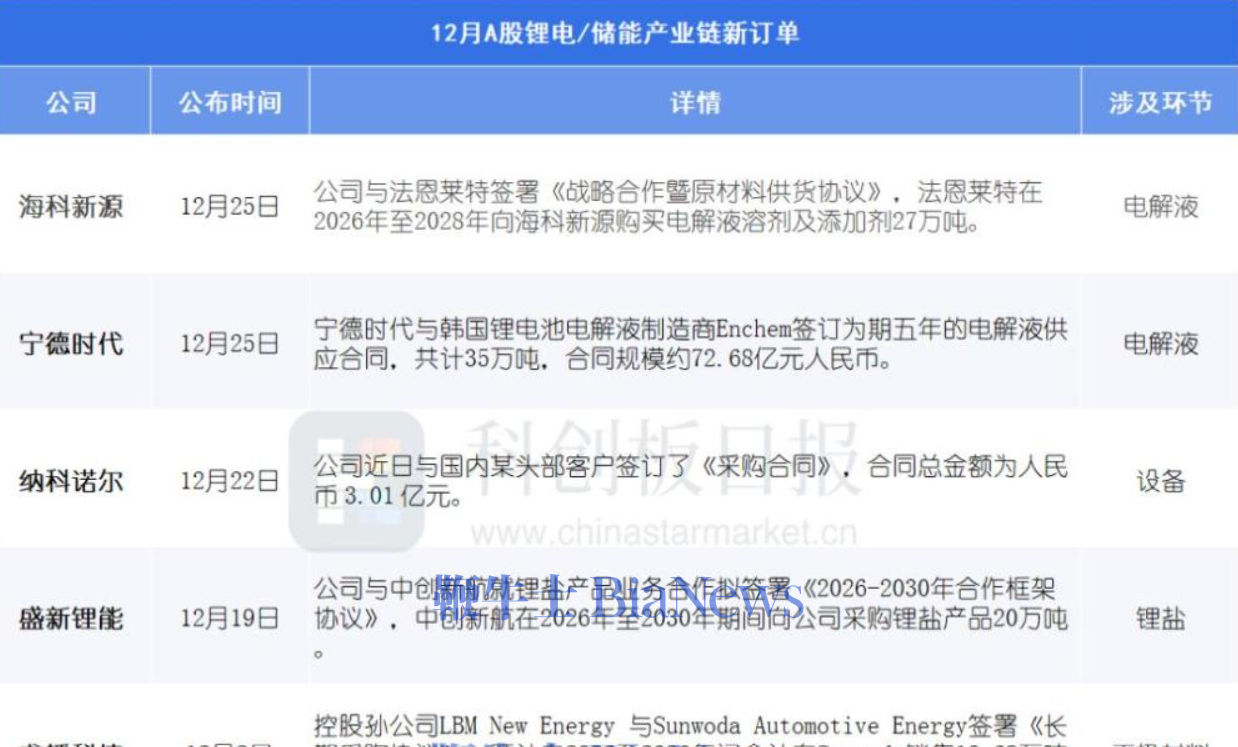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1402013531號
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1402013531號